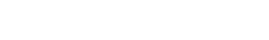今年两会,再次将中小学减负问题推向舆论的高潮。围绕着“减负”问题,人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问题的核心非常简单:教育部希望减负的美好愿望和家长们面对竞争想减却不敢减的巨大矛盾。
“减负”会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的后果,现在还难以看到。但是不少国家已经有了减负的先例,“减负”到底怎样,从他们身上我们或许可以一观一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减负的日本。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一个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日本几乎所有家庭都希望多出来的钱可以资助孩子上大学,于是,上大学的考试竞争变得异常激烈。
大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传导到整个基础教育,导致基础教育非常应试化,产生了包括“填鸭式教育”、“考试地狱”等一系列说法,这和中国很多家庭目前正在经历的情况有些类似。
所以,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而且这些成功大多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而不是挤过高考独木桥后获得的成功,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了,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吃这个苦呢?我们建设成就,不一定要从这条路才能取得吧?”
在民众压力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宽松教育”的政策,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把公立学校每周的上课时间、课程标准、课程大纲都降下来(缩减课本),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
其次,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不允许择校,具体来看是将学校集群化,学生只能进入某一个学校群,具体进哪一个学校,只能通过抽签的方式随机入学。
这些教育理念是不错的,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宽裕地、充实地成长,不要被考试的压力磨灭了天性。但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系列副作用。
首先,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减轻学生负担的政策,但是考试竞争压力并没有因此而降下来。
通过日本的人口数据,我们可以发现,1992年,日本18岁人口达到战后第二次婴儿潮高峰,之后,直至2014年的22年间,18岁人口从205万减少至118万,降幅达42%。
这段时间,考试竞争压力逐渐降低,但是在1976年至1990年(“宽松教育”政策的头15年),人口数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大学的扩招也没有跟上,高等教育录取率不断降低,考试竞争变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轻松了。
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下,有进取心的家长和家庭,几乎都是转向私立学校、民办教育机构,有些学生平时就上私立学校,课外还要去补习机构,去增加应试的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家庭负担变得非常重。
与此同时,家长可能也会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原本公办学校都能够解决所有事情,给家长更多选择空间之后,家长并不知道如何做更有益,所以会产生过度补习等一系列问题,整个日本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出也变得非常大。
直接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宽松教育”政策的因素可能是PISA测试,日本学生原先在数学、阅读等方面是很强的,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当中,一开始是领先的,但是“宽松教育”政策实施了十几年之后,日本学生在数学、阅读等方面的测试中排名连续下降。
于是,就有了教育评论家“全世界小学生都知道了,只有日本小孩不知道。”、“科技立国成为泡影”等说法。
提到减负,很多带着移居到加拿大这边的华人家长也有这种担心,他们看着加拿大小学里面老师动不动就是一句“孩子们回去好好玩吧”,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感。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加拿大孩子也是在宽松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为什么人家没有减负减成废物,反正都成了各行各业优秀的人才?
原来,加拿大的大学并不像国内大学那样采取统一考试入学模式,而是全部都是自主招生。学校可以从报考的学生里面挑选出最合适的学生。
而且,选材标准并不是完全依靠分数,而是要看很多很多其他东西,甚至按照有些中国人的话说,加拿大的大学就是“事多”。
一般来说,加拿大大学招生的时候主要看三个方面指标:
成绩(省考情况、平均成绩等)
社会活动情况(义工、实践经历)
推荐情况(特长、品质)
也就是说,加拿大孩子考大学的时候,爱好特长、社会实践和分数一样,能够帮助自己更进一步。
具体到招考中:
成绩平平但是滑雪很厉害,能不能进好大学?
可以的。
成绩平平但是平时乐于助人,已经成了当地社区的模范级公民,能不能进好大学?
可以的。
成绩平平但是文笔出色,能在准备的材料和面试中打动大学招生面试官,能不能进大学?
可以的。
这里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是综合衡量一个孩子的特点、性格、成长情况再来决定前面的路往那边走。环境决定了这里的孩子们虽然课业负担小但也不会成废物,因为他们将业余时间利用到自己成长的其他方面。
两边不同的环境也造成了孩子们截然不同的成长轨迹。
加拿大小学初中很轻闲,没什么压力,课程都是老师安排的;到了高中第二个年头(也就是10年级),就要根据你将来的职业意向自己选课,有些课程是为上大学准备的,有些是为上学院准备的,还有些是为高中毕业后直接工作准备的。
上了高中,会一年比一年紧张,不过与中国准备高考的学子相比,还是要轻松一些。最后进了大学,反而特别紧张。
加拿大整个教育环境都认为,小学、初中那种年纪不大的学生明明就是个孩子,为什么要逼他们做这做那?学校教育就应该以发觉潜能,启发创造力,开发兴趣为主,同时还要培养孩子的各方面的好品德,好习惯。
对比日本和加拿大的经验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
同样是减负,加拿大减轻了学业负担,却扩大了对孩子考察的范围,最终培育出各尽其才的优秀人才;反观日本的做法,单纯地缩短学时、课本,去除重点学校,反而会造成“国民素质降低”和“补习恶性竞争”的双重恶果。
在很多反对“减负”的家长看来,目前中国无疑是在走当年日本的老路,这才是他们真正担忧的原因。
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实现“加拿大式”的减负,在减负的同时,提高孩子综合素质,全面启发每个孩子的潜能,显然不仅是现在的改革能够做到的。这必然需要整个考核机制、教学内容,以及学校风气的全面转向,要做到这些,我们还有一大段路要走。